罗兰·巴特 | 为了让人感到疑虑而说的话
罗兰?巴尔特去年于色伊出版社出版的《恋人絮语》一书,如今有着巨大的印数。如果他没有出版这本书的话,他虽然被知识分子也就是被少数人所欣赏或贬低,但也许只能悄然无声地走过一个时期。
罗兰?巴尔特非常看重文化,他不知疲倦地关注搜寻这个符号即单词、那个结构即句子,不知疲倦地关注移动和晃动着的符号与结构,直到它们接受并最终承认说话所意味的东西,承认作为爱好者的这位钢琴手和绘画人的写作的严肃性一一他在词语的调色板上选择直至选定使颜色准确或注解正确的那个词,这些都使得这位研究者变成了一位涉猎广泛的作家。他因为对文本和言语活动的全新批评,在两年前被法兰西公学委任以开展文学符号学讲座。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科学,在巴尔特看来,一切都是符号,一切都是言语活动。问题是,任何言语活动最后都粘连着思想,粘连着智慧。词语最终都成为生发心理俗套的诱饵。在解释这种危险的同时,还需要为这种目的而求助于本世纪的智慧。而在这个某种社会幻灭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迫使我们要复查我们定见的世纪里,因为在阅读他的有时是晦涩的书籍的时候,我有在努力之后,在发现一种全新思想之后的快乐,于是,我便邀请罗兰?巴尔特来回答一些许多人都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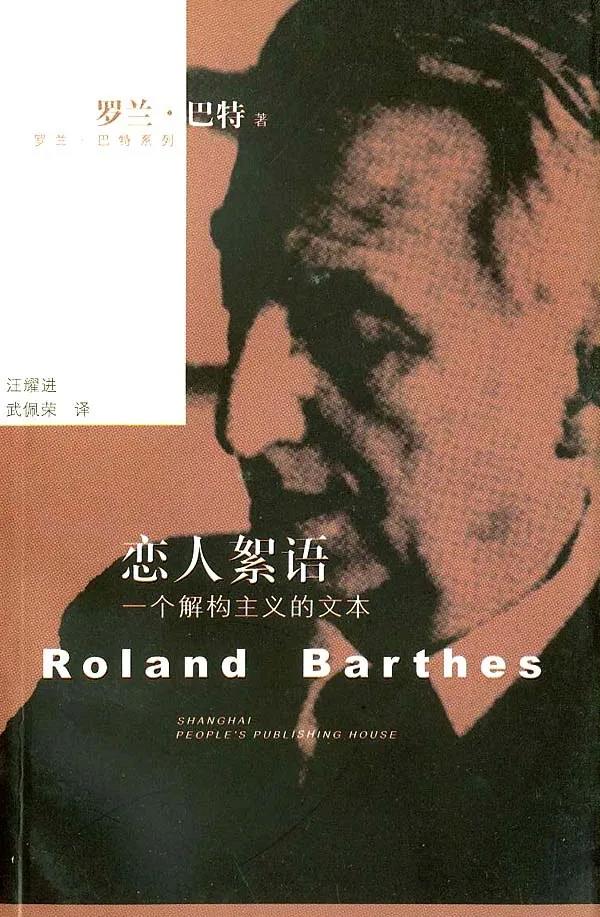
您说过,必须总是细心地倾听同时代人,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关于明天的预兆性符号。今天,难道人们不是已经可以感受到一种反犹太主义的泛起了吗?
未来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让人预先知道。但是,任何对于现在时的阅读,实际上都让人期待充满担忧和威胁的明天。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一如每个国家、每种文明、每种心理状态中都有的种族主义,总是活跃在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在法国,幸运的是,反犹太主义并不被重大政治决定所支持。但是,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企图存在于报刊和交谈之中。这种企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出现的事实,迫使知识分子应予以高度警惕。知识分子在这一方面可以起到一种正面的作用。绝对的规则,是监督人们在任何层面和在任何场合所说的东西,为的是永远不要使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即犹太人实际存在的情况。言语活动在任何时刻都必须绝对地清楚这种可怕的幽灵。
向浪漫主义求助,是比较含混的。浪漫主义包含着对个体性欲望的一些创造和颂扬力量,也包含着对理性主义者们的一种系统性对抗,而这一切都可以是正面的。但是,浪漫主义承载着反-知识论的神话,甚至承载着反犹太主义的某种风险。我们想一想后浪漫主义的德国吧。
至于神圣的事物,它包含着教徒的全部含混性。我确信,人类不可无神圣事物、无象征系统而生存。但是,人类面临两种风险:在教派层面上的蒙昧主义和由政治权力来承担的神圣事物。
我认为,面对所有这些危险,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希望,总是在边缘人一侧,从斗争到个人措施,都是如此。我想说的是,浪漫主义和神圣事物应该相互依附,但却是各自地跟随,原因是,一种价值一旦在像我们的社会一样属于群居的社会中形成,这种价值就成了挑衅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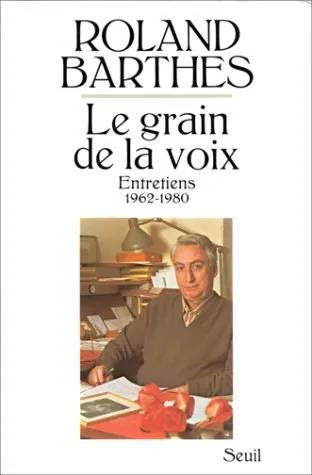
有人恰恰以带有很多挑衅、很多“清除”思想大师的口吻和总体上返回“正确理解力”的欲望来说话。现在,我们不是在知识分子劳改营,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您不觉得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法西斯主义推力吗?
您把法西斯主义的风险与这种精神状态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好地战斗的话,就要保留这些单词的意义。当然,在言语活动中、在话语中、在报刊中、在谈话中,有一些法西斯主义成分,它们变得充实,并逐渐给人这种悲剧印象。的确,有一种反-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主义,并且知识分子在充当其替罪羊,就像犹太人、鸡奸者、黑人那样。自浪漫主义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的诉讼周期性地出现。这种诉讼是因为“正确的判断力”而提起的,是因为强大的因循守旧观念而提起的,是因为人们在希腊所称的“公正舆论”——多数人认为应该思考的东西一一而提起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是多数人的阶级,但它是危险的:它摇摆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最终会与强力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制度结合在一起。无可争议的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具有一种历史的推力。这个阶级在上升,并尽力掌握权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阶级已经掌握了权力。
至于所谓的由舆论来清除思想大师,这是一种脆弱的恶作剧,它告诉大家思想大师是有的(这根本不是确定的),以便更好地左右他们的死亡。最少的辩证法,即最少的精巧,就可以使头脑非常聪明的人惊怕不已,以至于为了捍卫这种粗俗,他们借助于抹杀细微区别的正确判断力。
人们一般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智慧:数学与文学。您也这么认为吗?
一切取决于数学与文学的发展程度。在第一个层面上,对于这两种言语活动,有两种才干或是无才干。我认为,这是一种并非完全神秘的对立关系。但是,在第二个层面上,只要推动一下数学或是文学,各种阻拦就出现了。有一些相互作用、一些徒然交会。
在数学中,有一种丰富的巨大想象力,有一些重要的逻辑思维模式,这些逻辑思维最终以一种非常活跃的方式只在形式上形成,而无须去考虑内容。这一切都会使文学高度地感兴趣。而在文学中,有种活动越来越趋向数学思维的一些形式。在某个层面上,数学会与文学交相汇合。
对于您来讲,所有神话之未意味着什么呢?想象物之末和创造性之末又都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神话与宗教的衰弱是由历史的快速发展引起的,这种历史有时快速、有时缓慢地消耗各种价值。当前,出现了一种消耗的加速,即关于人类重大幻觉的强度和延迟的一种变化。但是,我要坚定地说,神话对于所有的社会都是必需的,为的是不引起撕裂。不过,神话不应该作为真实的借口被体验;它们应该在艺术中被体验,而艺术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错误之主谋。对于错误,艺术会将其昭示给人们。在这种时刻,错误便不再是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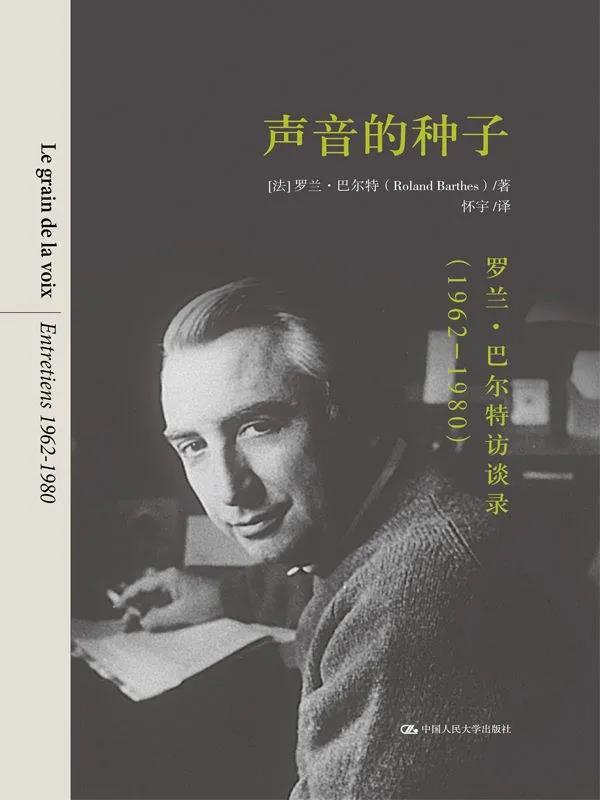
今天,您想过续写20年前出版的《神话》吗?在关系到《Elle》[1]这家杂志的方面,您在这本书中给出的形象已经过时了。如果暗玫瑰色曾在一段时间内是我们的偏好的话,那么,从1968年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特定兴趣。我们甚至经常谈论非常怪异的主题。
我有很长的时间没有阅读杂志了。但是,我相信,实际上《Elle》已经出现了很大变化。在像《EIle》这样的杂志层面,有着新闻写作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便是对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所突出。好的新闻写作,应该帮助读者建立起一种批评的和没有社会禁忌的意识。在《Elle》的情况里,刊物的变化和它所能包含的思考要素,显然与女性意识的发展有所联系。对于女性来说,重要的不是有一副高高的噪门儿一一就像一些女性运动有时所追求的那样一一而是有一副恰到好处的嗓门儿,一副接受巧妙的嗓门儿。
您说过,法国人都因为有拉辛而感到自豪,但对于没有莎士比亚而感到沮丧。爱情,在此,该像是一个法国式的、布局有序且有界限的花园吧?我们的英国式花园(爱情一激情)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我们有过英国式的花园吗?
法国那些伟大的古典作家,在强调嫉妒的同时,描述过爱情一激情。大致说来,他们是妄想狂。而德国人,例如海涅,可以说是强调伤害、怀恋、感情流露。实际上,这与法国传统是相当有别的。法国,有点错过了浪漫主义,这在其对爱情的态度方面有所表现。
那么,神意爱情呢?因为这种爱情是借助于祈祷的言语活动来进行的,您对巴尔扎克中篇小说《萨拉辛》所做的破释工作,为《新约全书》都提供了什么呢?
博舒哀[2]以绝对战斗的姿态说过,在言语活动上,不存在不分节的、不是公式化的祈祷。在这一方面,他攻击费纳龙[3]和那些神秘学说者,因为他们坚持说,纯粹的祈祷是处在言语活动之外、寓于绝对的不可磨灭之中的。神秘论总是代表着在言语活动方面的最为困难的经验。这便是神秘论让人感兴趣的原因。我们可以对《新约全书》进行一种结构分析的研究吗?依我说,是可以的。就我个人来讲,我曾对《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的几个文本做过两次简短的分析。但是,在结构分析只描述形式并停留在宗教讯息之中的情况下,不可能过于深入。文本就像是一种千层糕点(难道不是这样吗?):各种意义像糕点的层次那样叠合在一起。对于《新约全书》,做这样的分析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分析工作,在仔细研究过文本的所有组织层次之后,会让我们重新回到文字上来,而无须使文字抹杀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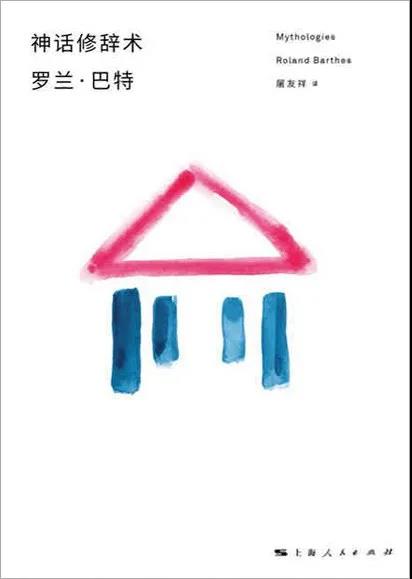
在《时尚系统》中,您说过,时尚除了作为意指系统之外,没有存在价值。您是否想以此来说明“告诉我你如何着装,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呢?
时尚是一种编码、一种言语活动。在被编码的言语活动与主体说这种言语活动的方式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在能力(懂得说这种言语活动和了解其编码)与运用[4](我们在说话时的所为)之间有一种关系。时尚真真切切就是编码,正是这种编码让我可以将时尚描述为“像是一种语言”[5]。有着一种个人的方式来讲述这种语言,它会迫使你按照一种人为的编码来说出一些个人的事情。时尚迫使你说出人们认为存在的东西,说出人们想与所有人的语言一起出现的东西。而我要说,这甚至就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定义。人注定要用其他人的语言来自我表白。请注意一下50年来的各种女性时尚。它们的变化涉及非常不同的色情。你看,我认为,时尚过于“文化”,不曾解放过身体。相反,当时尚尽力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审美价值时,我则认为它进步了。在这种时候,时尚尽力想象形式与颜色、类型和体型,因为它们都与人类的重大造型经验之保留着某种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与艺术之间有某种关系。
也与生存的艺术有某种关系。日本的生存艺术征服了您。您认为,在任何个人生存艺术之前,有无一种全民的生存艺术呢?
一种生存艺术可以是社会性的。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的生存艺术就不是令人不悦的,或者说,它就是全民的。我经常梦想,以描述的形式,在纸上构筑一种综合性的生存艺术,这种艺术能将具有非常不同的文明的所有成功的生存艺术特征汇聚在一起。
在我们这样的工业国家里,业余性难道不是一种自由的生存艺术吗?
绝对是,因为这种业余性强调的是作品的生产过程,而不是作为产品的作品。然而,我们处在由产品形成的一种文明之中,对生产感兴趣,就变成颠覆性的了。绘画,就有不少业余爱好者。这些爱好者对绘画有着极大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是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正确判断力”对业余性有着某种同情。这个时候,这种业余性并非一种惧怕,即它根据边缘人因此也是根据具有颠覆性的人所制造的那种惧怕。
您的新的感知方式,即您在字里行间进行解读的方式,难道它本身在最高层次上不是颠覆性的吗?
我认为,从我的层面来讲,认为我是覆性的,是过奖了。但是,我要说,从词源学上讲,我是在试图颠覆。也就是说,我试图无视一种因循守旧,无视一种现存的思维方式并想对它有所变动。这其中,不存在变革,不是的,而是试图欺骗各种事物、贬低各种事物,是使其变得更灵活些,是让人们听到一种疑虑,因此就总是在动摇所谓的自然性,即已经被固定的东西。
《EIle》,1978年12月4日,
弗朗索瓦·图尼耶(Fran?oise Tournier)整理
注 释
[1] 《Elle》:法国著名女性时尚杂志。该杂志在我国以《世界时装之苑》名称出版。——译注
[2] 博舒哀(Jacques-Bénign Bossuet,1627-1704):法国主教兼作家。——译注
[3] 费纳龙(Fran?oise Fénelon,1651-1715):法国神学家兼作家。——译注
[4] 能力(compétence)与运用(performance):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这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引入的概念,前者指一种潜在的知识准备和积累,后者指对前者的实际应用。——译注
[5] 这里的“语言”,仍然是指内在形式即结构。——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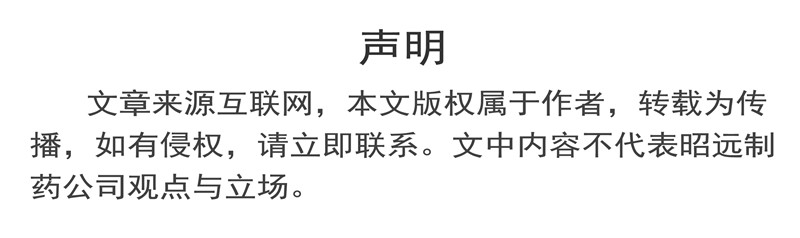
- 上一篇:生孩子在道德上是错的吗?
- 下一篇:十恶




